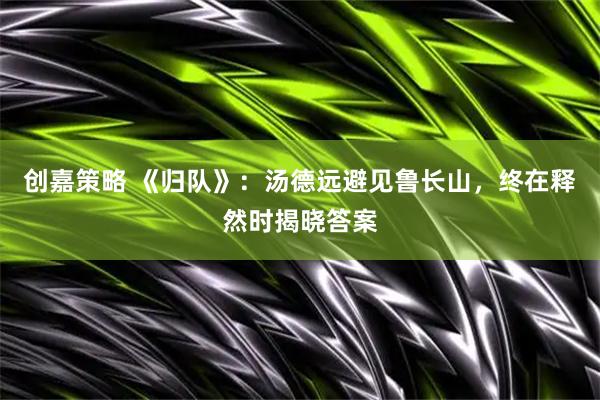
在《归队》的抗联群像中,汤德远的身影始终带着一层矛盾的底色。这个曾为掩护战友纵身跳崖的硬汉,却在与鲁长山重逢的路上屡次避而不见,直到儿子枉死的真相揭开,他如释重负的那一刻,观众才读懂这份逃避背后,藏着一个普通人在信仰与生存间的血泪挣扎。
一、避而不见的第一层枷锁:叛徒的自我烙印
劳工营里的妥协,成了汤德远一生的梦魇。当日军以父母性命相要挟,他颤抖着供出 “八棵松归队” 的秘密时,指尖沾染的不仅是笔墨,更是自我认定的 “叛徒” 烙印。此后每次与鲁长山的偶遇,他都像受惊的困兽般躲藏 —— 在松林镇的酒馆,他听见鲁长山熟悉的嗓音便翻窗逃离;在运粮队的队伍里,他看到鲁长山的身影就谎称肚子疼掉队。李乃文用细腻的演技将这份恐惧具象化:听到 “老山东” 三个字时骤然僵硬的脊背,与战友擦肩而过时不敢直视的眼神,连端碗的手都在微微颤抖。
展开剩余73%这份逃避,本质上是对自我价值的否定。鲁长山在他心中,早已不是单纯的战友,而是抗联精神的化身。当鲁长山带着战士们在山林里忍饥挨饿仍坚守信仰时,汤德远却在伪军的 “庇护” 下过着安稳日子,这种对比让他无地自容。就像他在日记里写的 “我不配再穿这身军装”,避见鲁长山,其实是在逃避那个背叛了信仰的自己。
二、逃避的深层根源:家庭羁绊下的生存抉择
如果说 “叛徒” 标签是汤德远逃避的外在枷锁,那么家庭的羁绊则是他内心的软肋。脱离劳工营后,汤德远化名 “王老实”,在肖铁林的安排下有了妻儿和小店,这份久违的安稳让他陷入两难 —— 一边是鲁长山代表的抗联使命,一边是怀中嗷嗷待哺的儿子。当鲁长山派人劝他归队时,他看着儿子熟睡的脸庞,最终还是选择了闭门不见。
这种选择背后,是小人物最真实的生存困境。剧中有这样一幕:汤德远给儿子做拨浪鼓,木槌敲击鼓面的声音里,突然混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,他瞬间将儿子紧紧搂在怀里,眼神里满是恐惧。对他而言,归队意味着再次置身险境,而他再也承受不起失去家人的痛苦。正如他对妻子说的 “我只想让你和孩子活着”,这份对安稳的渴望,让他在鲁长山面前筑起了一道名为 “逃避” 的高墙。
三、如释重负的转折点:儿子之死唤醒信仰
儿子的意外离世,成了打破这道高墙的惊雷。当汤德远发现儿子竟是因自己 “伪军白手套” 的身份,被日军当作诱饵杀害时,他抱着冰冷的尸体,终于明白:所谓的安稳不过是日军编织的谎言,没有国家的安稳,何来小家的平安。这一刻,他蹲在雪地里放声痛哭,泪水冲刷掉的不仅是悲伤,还有对生存的妥协。
这份彻骨的悲痛,化作了直面过去的勇气。当鲁长山再次找到他时,汤德远没有再躲藏,而是将儿子的拨浪鼓放在鲁长山面前,声音沙哑却坚定:“我想归队。” 他眼底的怯懦被决绝取代,曾经颤抖的双手此刻紧紧握住了枪杆。这种转变,不是突然的觉醒,而是积压已久的愧疚与愤怒的爆发 —— 他要为儿子报仇,更要赎回自己的罪孽。
四、释然背后的成长:从逃避者到归队人
汤德远最终的 “归队”,不仅是身体的回归,更是精神的救赎。他带着日军粮仓的布防图找到鲁长山时,两人没有多余的寒暄,鲁长山递给他一把枪,他接过的瞬间,仿佛重新找回了丢失的尊严。在炸粮仓的战斗中,汤德远冲在最前面,火焰映着他坚毅的脸庞,那个曾经逃避的 “王老实” 彻底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抗联战士汤德远。
这场迟来的重逢,让观众读懂:有时候逃避不是懦弱,而是普通人在绝境中的无奈抉择。汤德远避见鲁长山的日子里,其实一直在与自己的内心交战,直到儿子的死让他明白,真正的安稳不是苟且偷生,而是为信仰而战。正如剧中鲁长山所说 “活着,拼了命地活下去,活着就有希望”,汤德远的 “归队”,正是对这句话最深刻的诠释 —— 希望不仅在于活着,更在于带着信仰勇敢前行。
《归队》用汤德远的故事告诉我们,英雄从不是天生的。他们会犹豫、会恐惧、会逃避,但在关键时刻,总能冲破内心的枷锁,选择正确的方向。汤德远避而不见的背后,是一个普通人的血泪与挣扎,而他最终的释然与归队,更彰显了抗联精神的强大力量 —— 无论走多远,只要初心不忘,终能找到回家的路。
发布于:安徽省正规炒股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